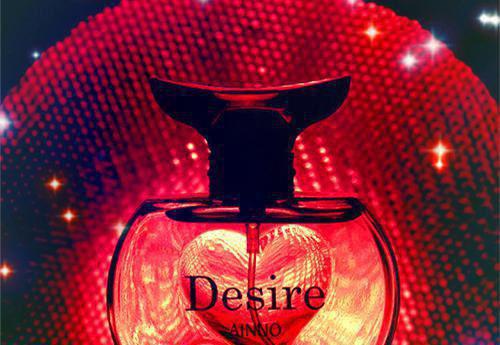母亲的缝纫机
母亲爱它,就像爱自己的女儿。一直以来,我就是这么认为的。依稀记得五岁那年,母亲踏着脚板,挺直了腰,缝纫机的“吱呀”声,伴随着一条宽大的棉布,织锦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我抱着那块又冰又滑的棉布,当着被子来看待。我称它为“黑被”。每到夏天,母亲便把它拿出,用搓衣板使劲上下来回搓动,肥皂冒出了许多泡泡,一会儿冒出一个,一会又消失一个,此消彼长,我时常会用塑料瓶,装上一小堆泡沫,用小圈儿吹出一个个五彩的泡泡,轻轻慢慢对着圈儿吹气,泡泡渐渐变大,摇晃着滑稽柔软的身体,在空中酝酿一下自己的“功力”,很快成了型,向高处飘散开去。
没有“黑被”,我是无论如何也睡不香的,只要翻过身来,摸不到“黑被”,我就会叫“妈,拿来!”此时母亲立即从睡梦中醒来,急忙寻找它的身影。“乖,妈妈给你盖上。”母亲极尽温柔的哄道。火热的夏季,我的头经常会冒汗,母亲经常会在我睡着的时候,拿了一方手帕,轻轻为我拭去整豆大的汗珠。而我,却安享在“黑被”的清凉之中,哪里知道,那一方手帕,也是母亲用缝纫机缝制的。
大概是受了母亲的影响,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我突然心血来潮,自个摸索着怎么缝一个枕头。打线、穿针,到转角处提起压轴,不知不觉中,踏板已经在我的脚上行云流水般上上晃动。想不到,第一次使用缝纫机的我,能如此迅速的上手,看那镶着金边的小枕头,我心里美滋滋的。
以后,随着学业的繁重,兴趣的转移,缝纫机仿佛从此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。我整日埋头学习,专注校田径队的训练,再长大些,便迷上了漫画,而母亲,更是在工作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,一丝不苟,仿佛,除了家庭与工作,缝纫机于她已是多余的。

十年春秋,十年辛酸,一晃十年过去了,仿佛,我已经长大成人,母亲的头上也多了几根白发。世事难料,病魔在高考之际侵袭我的身体。
母亲再次拉开盖上了胶布缝纫机,轻轻的擦拭、检查、实验,想不到,十年没用过缝纫机的母亲伸手仍然如此敏捷,每个动作,每条线痕,每个转角处,虽然不能与专业的缝纫工人相提并论,可还是看得出母亲于缝纫还是有不错的功底。
母亲再次拉开盖上了胶布缝纫机,轻轻的擦拭、检查、实验,想不到,十年没用过缝纫机的母亲伸手仍然如此敏捷,每个动作,每条线痕,每个转角处,虽然不能与专业的缝纫工人相提并论,可还是看得出母亲于缝纫还是有不错的功底.
又十几年过去了,这些年来,母亲憔悴了许多,而我的病又反复发作。每个晚上,母亲都会坐在缝纫机前,缝制睡衣、袋子、牛仔裤、被子,什么东西破了,她就缝什么;什么东西旧了,她就买新的布来做;什么东西她觉得做得起劲了,她就缝制什么!
起初,我还对她的作品啧啧称赞,可是日子长了,她把陪伴我的时间都用来缝缝补补上了,根本不理会我的感受。于是,一天晚上,我的火气终于爆发,把凳子朝缝纫机一摔,它便掉了一角。母亲看着那受了伤的缝纫机,低下头来,良久没有说话,继续含着泪,缝制着我明天要穿的睡衣.
借着明亮的灯光,我悄悄看着母亲的侧影。坐在缝纫机前的母亲,已经戴上了深度近视的眼镜,动作虽然麻利,却没有以前精准。母亲低着头,眼睛几乎要靠到针眼那里去了,无论怎样对准针眼,那线仿佛在捉弄母亲似的,那针也仿佛会动,就是不让母亲把线又快又准的穿过去。母亲的背不像以前那样直了,微微向前弯曲,身子也不如以往强壮,瘦弱了不少……
我轻轻的叹了气,眼神又转向电视机。
那天,母亲没有吃饭,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哭泣,我心里一直隐隐作痛,缝纫机重要还是我重要,其实答案早已明了,只是我太过自私了,不明白,母亲用她的爱,灌注在缝纫机上,为我缝制出一片母爱的天空!